水浒传的点评 20篇 每篇50字 左右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8 03:56:50
水浒传的点评 20篇 每篇50字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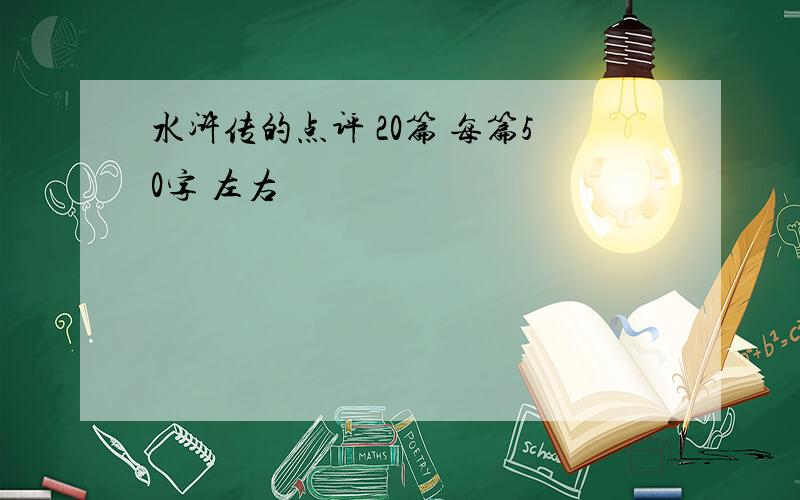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