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地位?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9 10:24:35
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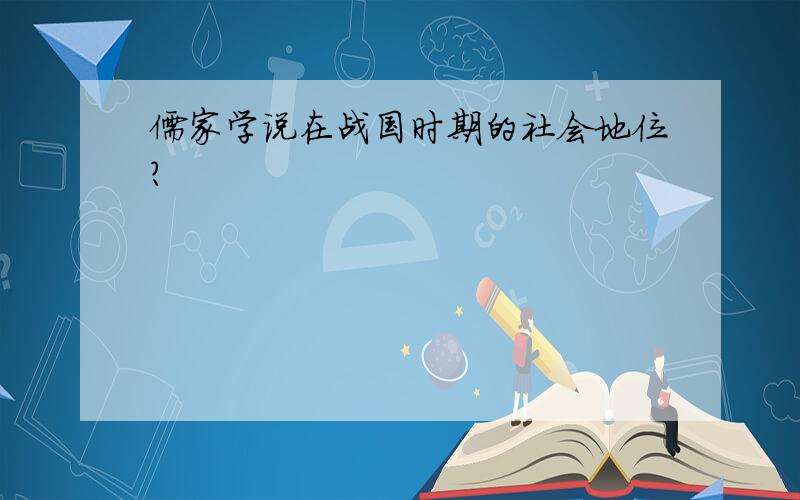
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主张:井田制,回归奴隶社会.王道礼教.
地位: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儒家并没有跟随历史的脚步,而是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在大争之世宣扬什么德治王道治理,完全背离了历史的潮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使用他们的主张.但是儒家在教育方面却有突出的作用,战国后期,儒家的学子占据了诸子百家的一半还多.
我个人观点:儒家思想垃圾!
一下是《大秦帝国》的原文
孟子喟然一叹:“奸佞当道,庶民倒悬,此皆苏秦之罪也.”
一言落点,稷下士子中便有嗡嗡议论之声,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瞄向了张仪.苏秦新丧,张仪容得孟子亵渎苏秦么?看那张仪,却是神色淡漠,径自饮酒.孟尝君却一眼看到,张仪的那根细亮的铁杖在案下抖动着!
齐宣王明知就里,又岔开笑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安定燕国?”
“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燕国自安.”
齐宣王听孟子再没有触及难堪话题,便松了一口气道:“先生所言,天下大道.敢问先生:如何便能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
孟子便微微皱起了眉头,苍老的语调竟是分外矜持:“上智但言大道.微末之技,利害之术,惟苏秦、张仪纵横者流所追逐也,孟轲不屑为之.”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目光便齐刷刷聚向了张仪!齐宣王也一时愣怔了.
“孟夫子名不虚传,果然是大伪无双也.”张仪应声而起,一句悠闲而犀利的评点,便使殿中轰然炸开,嗡嗡议论不绝——方今天下,谁敢直面指斥孟夫子“大伪无双”?若是别个名士,齐宣王也就阻止了,毕竟孟子是天下大家,如何能让他如此难堪?可这是名重天下的张仪,声威赫赫的秦国丞相,况且孟子挑衅在先,他如何能公然拦阻?
孟子极不舒坦,沉声问道:“足下便是张仪了?”
“微末之技,利害之术,纵横者流,张仪是也.”
孟子本来多饮了两爵,此刻更显得面红耳赤,竟是如坐针毡.四十余年来,孟子周游列国,虽然无一国敢用,名气却是越游越大,渐渐的也就不寄厚望于任何邦国,悠悠然成了一个超脱传道的大宗师.如此一来,反倒是放开说话无所顾忌,正合了孟子的傲岸本性,也使孟子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孟子资望更深,各国皆奉为大贤宗师,孟子便更是挥洒自如,往往对陪宴士子与官员不屑一顾,只与君王问对应答,俨然布衣王侯一般.常常是宴席结束论战散场,孟子才问万章:“今日来者都有何人?论辩者究是那家弟子?”若非万章一般弟子因了要记录孟子言谈,刻意记下了应对陪同者姓名而后告孟子,孟子便当真是目中无人一片混沌了.今日入得临淄,孟子也是对大片冠带不屑一顾,甚至连丈许之遥的主陪——张仪与孟尝君,也是漫不经心,没有看进眼里.也就是说,孟子压根儿就没想到能在临淄碰上张仪.及至那个铁拐高冠者站了起来,甩出“大伪无双”四字,竟是掷地有声!孟子才蓦然闪念,此人必是张仪无疑.
仿佛便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孟子被誉为“大才雄辩,天下无对”,张仪则有“天下第一利口”名号,偏这两人但见便有口舌,竟是生死纠缠的冤家一般.二十多年前,孟子在大梁讥讽纵横家是“妾妇之道”,就被刚刚出山的张仪卒不及防的痛斥了一顿.从此,孟子便对张仪苏秦厌恶之极,内心却也实在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虽然,孟子还是每说大道必骂纵横策士,但却再也没有说过“妾妇之道纵横家”那句话了.今日原本是孟子说得口滑,便滑上了贬损纵横策士的老路子,却不意偏偏撞上了张仪在场,又遇苏秦新丧,孟子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虽则心中忐忑,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致歉的习惯,振作心神,一开口便气度沉雄:“大道至真,不涉得失.末技卑微,惟言利害.以利取悦于人,以害威慑于人,此等蛊惑策士,犹辩真伪之说,岂非天下笑谈耳?”
“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竟是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竟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便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便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便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最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做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张仪一阵嬉笑怒骂,大殿中竟是鸦雀无声,惟闻张仪那激越的声音在绕梁游走:“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是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干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让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干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的真相!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呵哈哈哈哈哈哈哈……”末了,张仪竟是仰天大笑.
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惟闻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孟子想反驳,想痛斥,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辞无处着力,想愤然站起拂袖而去以示不屑,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眼看张仪张牙舞爪哈哈长笑,孟子竟是不能立即做振聋发聩的反击,论战如斯,便是全军覆没,煌煌儒家,赫赫孟轲,岂容得如此羞辱?大急之下,但闻“哇——!”的一声,孟子一口鲜血竟喷出两丈多远!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卒不及防,身上竟扑满了鲜血,连并排的齐宣王酒案上也溅满了血滴!
“老师——!”儒家弟子们呐喊一声,一齐扑向孟子.王殿顿时大乱,齐宣王铁青着脸色大喝:“孟尝君,太医!”孟尝君憋住笑意,便回身高喊:“太医!快!太医——!”奇怪的是,稷下学宫的一百多个名士竟都无动于衷,默然的看着忙乱的内侍侍女,与一片哭喊的儒家弟子,竟是没有一个人上前照拂.
孟子被抬走了.齐宣王拂袖而去了.盛大的接风宴席落得如此收场,朝臣们竟是一片愣怔.稷下学宫的名士们却围了过来,齐齐的向张仪肃然一躬,便默默散去了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治国为政,仁与不仁,容与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边想边说,不甚流畅然却极富力度,“先说仁与不仁.何为仁政?孔夫子一生讲仁,儒家几百年讲仁,然却从未给‘仁’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作为国家大政,对民众仁是仁,抑或对贵族仁是仁?天下郡县一治民众安居乐业是仁,抑或诸侯裂土刀兵连绵是仁?儒家从来不说.大约也不愿意说.说清楚了,也就没那个‘仁’了.法家何以反对儒家之仁?从根本上说,正是反对此等大而无当又宽泛无边的滥仁!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真正确立仁政界标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韩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爱民,大仁不仁.韩子有言,严家无败虏,而慈母有败子.秦法不行救济,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却激发民众奋发,遏制罪行膨胀,一举而达大治,又是大仁!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为大仁?说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众富庶,国家强盛,就是大仁.欲达大仁之境,就要摒弃儒家之滥仁.就要荡涤污秽,清灭蠹虫,除掉害群之马!”
宽阔敞亮的书房静如幽谷,嬴政皇帝的声音持续地回荡着.
“再说容与不容.容者,兼存也,共处也.然则,天下有善恶正邪,人众有利害纠葛,政道有变法复辟,学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纷纭纠葛之下,任是国家,任是学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讲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讲兼爱,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讲爱民,何以不容疲民游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处:大道同则容,大道不同则不容.兼容一切,无异于污泥浊水,无异于毁灭文明.
今我大秦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而这棵大树的根基,却只能扎在脚下这方老土之中.当此之时,这棵大树要壮盛生长,便容不得虫蚁蛇鼠败叶残枝.否则,大秦的根基便会腐烂,大树便会轰然折断.其时也,六国贵族之复辟势力,容得大秦新政么?不会.决然不会!若我等君臣为彰显兼容之量,而听任复辟言行泛滥.误国也,误民也,误华夏文明也.战国之世血流成海,泪洒成河,尸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诫我等:复辟裂土乃千古罪人么?儒家以治史为癖好.嬴政宁肯被儒家在史书上将嬴政写成暴君,写成虎狼,也绝不会用国家安危去换一个仁政虚名,绝不会用文明存亡去换一个兼容,换一个海纳!”
大臣们都静静地听着,忘记了任何呼应.嬴政皇帝罕见地说如此长话,却始终没有暴躁的怒气,始终都是平静而有力.在静如幽谷的大书房,嬴政皇帝转入了最后的决断申明:“至于如何处置儒家罪行,朕意已决:依法论罪,一人不容.何以如此?一则,大秦法行在先,触法理当惩治.二则,儒家既不愿做兴盛文明之大旗,便教他做鼓噪复辟之大旗.朕要严惩儒家以告诫天下:任准要复辟,先得踏过大秦法治这一关.”
几百儒生,几个博士,几万贵族,就想颠覆大秦,就想复辟旧制,先生不觉是螳臂当车么?朕还要告诉你,你这个博士,你等那个儒家,其实并没有真实学问.自孔孟以后,儒家关起门自吹自擂,不走天下,不读百家,狭隘又迂腐,论国论政全无半点雄风,朕为之寒心,天下嗤之以鼻,儒家若不再生,必将自取灾亡也!”一席嬉笑怒骂的雄辩戛然而止了
儒家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主张:井田制,回归奴隶社会.王道礼教.
地位: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儒家并没有跟随历史的脚步,而是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在大争之世宣扬什么德治王道治理,完全背离了历史的潮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使用他们的主张.但是儒家在教育方面却有突出的作用,战国后期,儒家的学子占据了诸子百家的一半还多.
我个人观点:儒家思想垃圾!
一下是《大秦帝国》的原文
孟子喟然一叹:“奸佞当道,庶民倒悬,此皆苏秦之罪也.”
一言落点,稷下士子中便有嗡嗡议论之声,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瞄向了张仪.苏秦新丧,张仪容得孟子亵渎苏秦么?看那张仪,却是神色淡漠,径自饮酒.孟尝君却一眼看到,张仪的那根细亮的铁杖在案下抖动着!
齐宣王明知就里,又岔开笑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安定燕国?”
“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燕国自安.”
齐宣王听孟子再没有触及难堪话题,便松了一口气道:“先生所言,天下大道.敢问先生:如何便能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
孟子便微微皱起了眉头,苍老的语调竟是分外矜持:“上智但言大道.微末之技,利害之术,惟苏秦、张仪纵横者流所追逐也,孟轲不屑为之.”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目光便齐刷刷聚向了张仪!齐宣王也一时愣怔了.
“孟夫子名不虚传,果然是大伪无双也.”张仪应声而起,一句悠闲而犀利的评点,便使殿中轰然炸开,嗡嗡议论不绝——方今天下,谁敢直面指斥孟夫子“大伪无双”?若是别个名士,齐宣王也就阻止了,毕竟孟子是天下大家,如何能让他如此难堪?可这是名重天下的张仪,声威赫赫的秦国丞相,况且孟子挑衅在先,他如何能公然拦阻?
孟子极不舒坦,沉声问道:“足下便是张仪了?”
“微末之技,利害之术,纵横者流,张仪是也.”
孟子本来多饮了两爵,此刻更显得面红耳赤,竟是如坐针毡.四十余年来,孟子周游列国,虽然无一国敢用,名气却是越游越大,渐渐的也就不寄厚望于任何邦国,悠悠然成了一个超脱传道的大宗师.如此一来,反倒是放开说话无所顾忌,正合了孟子的傲岸本性,也使孟子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孟子资望更深,各国皆奉为大贤宗师,孟子便更是挥洒自如,往往对陪宴士子与官员不屑一顾,只与君王问对应答,俨然布衣王侯一般.常常是宴席结束论战散场,孟子才问万章:“今日来者都有何人?论辩者究是那家弟子?”若非万章一般弟子因了要记录孟子言谈,刻意记下了应对陪同者姓名而后告孟子,孟子便当真是目中无人一片混沌了.今日入得临淄,孟子也是对大片冠带不屑一顾,甚至连丈许之遥的主陪——张仪与孟尝君,也是漫不经心,没有看进眼里.也就是说,孟子压根儿就没想到能在临淄碰上张仪.及至那个铁拐高冠者站了起来,甩出“大伪无双”四字,竟是掷地有声!孟子才蓦然闪念,此人必是张仪无疑.
仿佛便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孟子被誉为“大才雄辩,天下无对”,张仪则有“天下第一利口”名号,偏这两人但见便有口舌,竟是生死纠缠的冤家一般.二十多年前,孟子在大梁讥讽纵横家是“妾妇之道”,就被刚刚出山的张仪卒不及防的痛斥了一顿.从此,孟子便对张仪苏秦厌恶之极,内心却也实在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虽然,孟子还是每说大道必骂纵横策士,但却再也没有说过“妾妇之道纵横家”那句话了.今日原本是孟子说得口滑,便滑上了贬损纵横策士的老路子,却不意偏偏撞上了张仪在场,又遇苏秦新丧,孟子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虽则心中忐忑,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致歉的习惯,振作心神,一开口便气度沉雄:“大道至真,不涉得失.末技卑微,惟言利害.以利取悦于人,以害威慑于人,此等蛊惑策士,犹辩真伪之说,岂非天下笑谈耳?”
“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竟是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竟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便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便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便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最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做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张仪一阵嬉笑怒骂,大殿中竟是鸦雀无声,惟闻张仪那激越的声音在绕梁游走:“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是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干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让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干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的真相!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呵哈哈哈哈哈哈哈……”末了,张仪竟是仰天大笑.
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惟闻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孟子想反驳,想痛斥,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辞无处着力,想愤然站起拂袖而去以示不屑,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眼看张仪张牙舞爪哈哈长笑,孟子竟是不能立即做振聋发聩的反击,论战如斯,便是全军覆没,煌煌儒家,赫赫孟轲,岂容得如此羞辱?大急之下,但闻“哇——!”的一声,孟子一口鲜血竟喷出两丈多远!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卒不及防,身上竟扑满了鲜血,连并排的齐宣王酒案上也溅满了血滴!
“老师——!”儒家弟子们呐喊一声,一齐扑向孟子.王殿顿时大乱,齐宣王铁青着脸色大喝:“孟尝君,太医!”孟尝君憋住笑意,便回身高喊:“太医!快!太医——!”奇怪的是,稷下学宫的一百多个名士竟都无动于衷,默然的看着忙乱的内侍侍女,与一片哭喊的儒家弟子,竟是没有一个人上前照拂.
孟子被抬走了.齐宣王拂袖而去了.盛大的接风宴席落得如此收场,朝臣们竟是一片愣怔.稷下学宫的名士们却围了过来,齐齐的向张仪肃然一躬,便默默散去了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治国为政,仁与不仁,容与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边想边说,不甚流畅然却极富力度,“先说仁与不仁.何为仁政?孔夫子一生讲仁,儒家几百年讲仁,然却从未给‘仁’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作为国家大政,对民众仁是仁,抑或对贵族仁是仁?天下郡县一治民众安居乐业是仁,抑或诸侯裂土刀兵连绵是仁?儒家从来不说.大约也不愿意说.说清楚了,也就没那个‘仁’了.法家何以反对儒家之仁?从根本上说,正是反对此等大而无当又宽泛无边的滥仁!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真正确立仁政界标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韩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爱民,大仁不仁.韩子有言,严家无败虏,而慈母有败子.秦法不行救济,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却激发民众奋发,遏制罪行膨胀,一举而达大治,又是大仁!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为大仁?说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众富庶,国家强盛,就是大仁.欲达大仁之境,就要摒弃儒家之滥仁.就要荡涤污秽,清灭蠹虫,除掉害群之马!”
宽阔敞亮的书房静如幽谷,嬴政皇帝的声音持续地回荡着.
“再说容与不容.容者,兼存也,共处也.然则,天下有善恶正邪,人众有利害纠葛,政道有变法复辟,学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纷纭纠葛之下,任是国家,任是学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讲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讲兼爱,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讲爱民,何以不容疲民游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处:大道同则容,大道不同则不容.兼容一切,无异于污泥浊水,无异于毁灭文明.
今我大秦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而这棵大树的根基,却只能扎在脚下这方老土之中.当此之时,这棵大树要壮盛生长,便容不得虫蚁蛇鼠败叶残枝.否则,大秦的根基便会腐烂,大树便会轰然折断.其时也,六国贵族之复辟势力,容得大秦新政么?不会.决然不会!若我等君臣为彰显兼容之量,而听任复辟言行泛滥.误国也,误民也,误华夏文明也.战国之世血流成海,泪洒成河,尸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诫我等:复辟裂土乃千古罪人么?儒家以治史为癖好.嬴政宁肯被儒家在史书上将嬴政写成暴君,写成虎狼,也绝不会用国家安危去换一个仁政虚名,绝不会用文明存亡去换一个兼容,换一个海纳!”
大臣们都静静地听着,忘记了任何呼应.嬴政皇帝罕见地说如此长话,却始终没有暴躁的怒气,始终都是平静而有力.在静如幽谷的大书房,嬴政皇帝转入了最后的决断申明:“至于如何处置儒家罪行,朕意已决:依法论罪,一人不容.何以如此?一则,大秦法行在先,触法理当惩治.二则,儒家既不愿做兴盛文明之大旗,便教他做鼓噪复辟之大旗.朕要严惩儒家以告诫天下:任准要复辟,先得踏过大秦法治这一关.”
几百儒生,几个博士,几万贵族,就想颠覆大秦,就想复辟旧制,先生不觉是螳臂当车么?朕还要告诉你,你这个博士,你等那个儒家,其实并没有真实学问.自孔孟以后,儒家关起门自吹自擂,不走天下,不读百家,狭隘又迂腐,论国论政全无半点雄风,朕为之寒心,天下嗤之以鼻,儒家若不再生,必将自取灾亡也!”一席嬉笑怒骂的雄辩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