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在哲学中是什么意思?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6 20:08:12
“形而上学”在哲学中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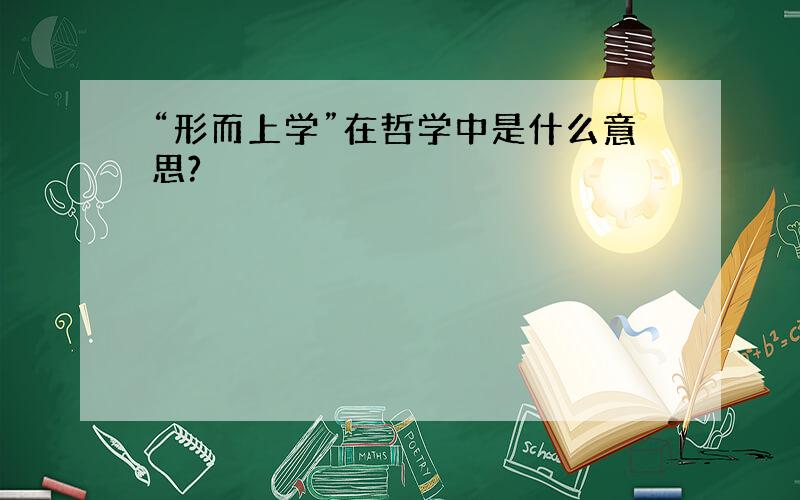
形而上学是哲学术语.
欧洲语言中的“形而上学”来自希腊语,如英语的“metaphysics”.这一词原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形而上学也叫“第一哲学”,如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也称为《形而上学沉思录》.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第一部分,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以树枝来比喻.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
形而上学的问题通常都是充满争议而没有确定的结论的.这一部份是因为经验事实所累积的资料,做为人类知识的最大宗,通常无法解决形上学争议;另一部份是因为形上学家们所使用的词语时常混淆不清,他们的争论因而是一笔各持已见但却没有交集的烂帐.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们反对某些形上学议题.他们认为某些形上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通俗的讲,形而上学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指研究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有时也指研究哲学的本体论.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只讲形式,不究实质,这就是形而上学
查出《易经》原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喜.朦胧觉得,形而上比较虚,形而下比较实,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形而上是指思维和宏观的属于虚的范畴;形而上学则是指认识事物走到了极端,是僵化的.老子有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为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指道,既是指哲学方法,又是指思维活动.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可以捉摸到的东西或器物.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5423.html
西方形而上学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它潜伏于米利都学派,发萌于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完成于亚里士多德.而在亚里士多德建成形而上学之后,立刻又面临反形而上学倾向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即各种人生哲学(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折中主义等等)将形而上学拉下“第一哲学”的宝座,直到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信仰结合成基督教神学,并在新的基础上建成更为复杂的基督教经院形而上学.然而,经院形而上学同样也包含着自身解体的种子,并从中孕育出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欧洲近代哲学的主流则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和解构形而上学的冲突中展现出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理论(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等)在休谟那里全军覆没,却在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语).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通常被看做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从此以后,西方形而上学就走在一条逐渐没落和淡化的道路上,从马克思、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组成了布朗肖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葬礼行列”.但奇怪的是,每当有人宣称形而上学已经完结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指出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蒯因则看出任何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本体论的承诺”),因而虽然许多人被依次宣布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却始终像一个“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分析形而上学在西方不断产生又不断覆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由两个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离的要素构成的,一个是规范性,一个是超越性.形而上学首先是规范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建立了第一个形而上学,正是由于他在具有最典型的规范性的语言概念系统中确定了一切规范的根本基础,即关于“是”的一整套精密规定,也就是“本体论”(“是论”).但这种规范性正因为是一切规范性的根本基础,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规范性,而是高于一切规范性的规范性,也就是“超越的”规范性,它需要一种提升,一种不断向高处追求的力量.西方哲学自从泰勒斯以来就一直处于这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各种不够高的规范性,如各种“始基”(水、火、气、数、“种子”、原子等等),各种“相”(理念),被找到之后又被抛弃、被超越了.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作为是的是”,或“是本身”,这是最高的规范性.于是他着手来建立一门关于“是本身”的学问,分析各种不同的“是”以及“是之为是”,这就是“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
因此形而上学本身一开始就包含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一种超越了的规范性和一种得到规范的超越性.规范性若不超越,它就是一般的甚至低层次的规范性,而达不到最高的规范性;超越性若不得到规范,它就是一种盲目的超越,最终会超越到不可规范甚至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那里去,也无法建立形而上学.低层次的规范性不是完整的规范性,最终会是零散的、杂乱无章的,因而是没有系统规范的;盲目的超越性也不是真正的超越性,最终会受制于某种尚不知道的低层次的束缚(如本能欲望之类).规范性有赖于超越性才得以建立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差异和杂多的泥潭中而无法成形;超越性只有借助于一定的规范才获得自己的支点,才得以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像在真空中扇动翅膀,一步都不能超升.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然而,这两方面同时又是矛盾冲突的.规范性本身就是对想要超越它的一切冲动的削平和制止,否则规范就被冲决了、解构了.在最高规范中,一切超越的冲动都平息了,它所构成的体系就是一个最终的绝对静止的体系(如黑格尔的体系).反之,所谓超越性首先就意味着对现有规范的打破和超出,而在最高的超越性中,一切规范都不足以表达超越的最终目标,这就导致形而上学的整个解体.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规范性和超越性交替上升的历史.每当人的思维由于超越现有规范而上达一个最高的规范时,形而上学就形成了;而当人的思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超越维度而超出原先的最高规范时,反形而上学就出现了.但反形而上学同样也必须在这一新的维度中寻求新的规范性,并经历新一轮的从低级规范超越到高级规范的历程,最后再次达到一种新的最高的形而上学规范,于是新的形而上学又再次建立起来,或者说“复辟”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的命运,但这命运自身就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即形而上学本身包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种子;反过来说,这反形而上学的种子正因为要反形而上学,所以必须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否则它根本动摇不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所以它不仅没有反掉形而上学,反而推进了形而上学向更高层次迈进.
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这种纠缠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纠缠.按照西方传统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在这里,“理性”就是“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字本身含有规范、语言、表达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又被译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说话这种活动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聚集”活动,即把各种杂多东西集合在一起加以展示的活动(这一点对于西方的时间性的拼音语言来说更容易了解),因而它必然是对杂多东西的超越.所以希腊人表达理性除了逻各斯这个词之外,还有“努斯”(Nous)这个词,它第一次由阿那克萨哥拉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认为它是在整个世界之外能动地推动世界的精神力量;在柏拉图那里则意味着精神的自动性和自发性.实际上,努斯和逻各斯在希腊人心目中是人的双重本质,它们分别代表人的存在和语言,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语言之家”,这双方是一刻也不可分离的.人最根本的存在冲动当然是追求自己的自动自发的自由,但这种冲动与动物的本能不同,就在于它具有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因而赋予了自由的自发冲动以规范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誓言、诺言,最后是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和逻辑确定性的社会语言.当人对自由的追求上升到要把握整个世界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层次时,人对语言规范性的探讨也就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层次.但与此同时,人的自由追求永远也不会甘心于长期受到某种规范性、哪怕是最高规范性的束缚,当它在最高规范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所可能有的一切目标之后,就开始想要对这种最高规范本身加以超越,以便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目标了.而对这更高目标的追求本身又有自己的新的规范.这就是为什么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永远交织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其矛盾的深层原因.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所谓“后现代”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决不可能意味着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历史的垃圾,而恰好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的一种发展方式.形而上学如同哈姆莱特的父王的幽灵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召唤一位历史性人物来“重整乾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后现代”思潮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冲动的彻底消失,假如“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灭使西方的逻各斯精神(包括逻辑精神)本身也遭到了彻底的覆灭,假如西方的努斯精神完全成了一种动物式的“怎么都行”的盲目冲撞,那将是人性的堕落和隳沉.我相信,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初衷决不会是这样,而是想要更大地发挥人的自发性的自由本性,摆脱现有一切规范性的束缚,把人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一些过激的提法,如对“人性”、“理性”等等基本规范的解构,只不过意味着他们对现有规范的不满和突破,而这种突破将不会是没有结果的,只是他们现在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果而已.
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所以,对于各个阶段上的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我们都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去研究他们、理解他们,为的是能真正超越他们.
欧洲语言中的“形而上学”来自希腊语,如英语的“metaphysics”.这一词原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形而上学也叫“第一哲学”,如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也称为《形而上学沉思录》.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第一部分,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以树枝来比喻.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
形而上学的问题通常都是充满争议而没有确定的结论的.这一部份是因为经验事实所累积的资料,做为人类知识的最大宗,通常无法解决形上学争议;另一部份是因为形上学家们所使用的词语时常混淆不清,他们的争论因而是一笔各持已见但却没有交集的烂帐.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们反对某些形上学议题.他们认为某些形上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通俗的讲,形而上学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指研究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有时也指研究哲学的本体论.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只讲形式,不究实质,这就是形而上学
查出《易经》原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喜.朦胧觉得,形而上比较虚,形而下比较实,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形而上是指思维和宏观的属于虚的范畴;形而上学则是指认识事物走到了极端,是僵化的.老子有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为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指道,既是指哲学方法,又是指思维活动.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可以捉摸到的东西或器物.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5423.html
西方形而上学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它潜伏于米利都学派,发萌于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完成于亚里士多德.而在亚里士多德建成形而上学之后,立刻又面临反形而上学倾向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即各种人生哲学(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折中主义等等)将形而上学拉下“第一哲学”的宝座,直到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信仰结合成基督教神学,并在新的基础上建成更为复杂的基督教经院形而上学.然而,经院形而上学同样也包含着自身解体的种子,并从中孕育出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欧洲近代哲学的主流则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和解构形而上学的冲突中展现出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理论(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等)在休谟那里全军覆没,却在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语).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通常被看做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从此以后,西方形而上学就走在一条逐渐没落和淡化的道路上,从马克思、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组成了布朗肖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葬礼行列”.但奇怪的是,每当有人宣称形而上学已经完结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指出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蒯因则看出任何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本体论的承诺”),因而虽然许多人被依次宣布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却始终像一个“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分析形而上学在西方不断产生又不断覆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由两个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离的要素构成的,一个是规范性,一个是超越性.形而上学首先是规范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建立了第一个形而上学,正是由于他在具有最典型的规范性的语言概念系统中确定了一切规范的根本基础,即关于“是”的一整套精密规定,也就是“本体论”(“是论”).但这种规范性正因为是一切规范性的根本基础,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规范性,而是高于一切规范性的规范性,也就是“超越的”规范性,它需要一种提升,一种不断向高处追求的力量.西方哲学自从泰勒斯以来就一直处于这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各种不够高的规范性,如各种“始基”(水、火、气、数、“种子”、原子等等),各种“相”(理念),被找到之后又被抛弃、被超越了.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作为是的是”,或“是本身”,这是最高的规范性.于是他着手来建立一门关于“是本身”的学问,分析各种不同的“是”以及“是之为是”,这就是“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
因此形而上学本身一开始就包含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一种超越了的规范性和一种得到规范的超越性.规范性若不超越,它就是一般的甚至低层次的规范性,而达不到最高的规范性;超越性若不得到规范,它就是一种盲目的超越,最终会超越到不可规范甚至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那里去,也无法建立形而上学.低层次的规范性不是完整的规范性,最终会是零散的、杂乱无章的,因而是没有系统规范的;盲目的超越性也不是真正的超越性,最终会受制于某种尚不知道的低层次的束缚(如本能欲望之类).规范性有赖于超越性才得以建立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差异和杂多的泥潭中而无法成形;超越性只有借助于一定的规范才获得自己的支点,才得以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像在真空中扇动翅膀,一步都不能超升.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然而,这两方面同时又是矛盾冲突的.规范性本身就是对想要超越它的一切冲动的削平和制止,否则规范就被冲决了、解构了.在最高规范中,一切超越的冲动都平息了,它所构成的体系就是一个最终的绝对静止的体系(如黑格尔的体系).反之,所谓超越性首先就意味着对现有规范的打破和超出,而在最高的超越性中,一切规范都不足以表达超越的最终目标,这就导致形而上学的整个解体.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规范性和超越性交替上升的历史.每当人的思维由于超越现有规范而上达一个最高的规范时,形而上学就形成了;而当人的思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超越维度而超出原先的最高规范时,反形而上学就出现了.但反形而上学同样也必须在这一新的维度中寻求新的规范性,并经历新一轮的从低级规范超越到高级规范的历程,最后再次达到一种新的最高的形而上学规范,于是新的形而上学又再次建立起来,或者说“复辟”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的命运,但这命运自身就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即形而上学本身包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种子;反过来说,这反形而上学的种子正因为要反形而上学,所以必须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否则它根本动摇不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所以它不仅没有反掉形而上学,反而推进了形而上学向更高层次迈进.
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这种纠缠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纠缠.按照西方传统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在这里,“理性”就是“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字本身含有规范、语言、表达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又被译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说话这种活动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聚集”活动,即把各种杂多东西集合在一起加以展示的活动(这一点对于西方的时间性的拼音语言来说更容易了解),因而它必然是对杂多东西的超越.所以希腊人表达理性除了逻各斯这个词之外,还有“努斯”(Nous)这个词,它第一次由阿那克萨哥拉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认为它是在整个世界之外能动地推动世界的精神力量;在柏拉图那里则意味着精神的自动性和自发性.实际上,努斯和逻各斯在希腊人心目中是人的双重本质,它们分别代表人的存在和语言,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语言之家”,这双方是一刻也不可分离的.人最根本的存在冲动当然是追求自己的自动自发的自由,但这种冲动与动物的本能不同,就在于它具有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因而赋予了自由的自发冲动以规范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誓言、诺言,最后是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和逻辑确定性的社会语言.当人对自由的追求上升到要把握整个世界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层次时,人对语言规范性的探讨也就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层次.但与此同时,人的自由追求永远也不会甘心于长期受到某种规范性、哪怕是最高规范性的束缚,当它在最高规范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所可能有的一切目标之后,就开始想要对这种最高规范本身加以超越,以便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目标了.而对这更高目标的追求本身又有自己的新的规范.这就是为什么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永远交织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其矛盾的深层原因.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所谓“后现代”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决不可能意味着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历史的垃圾,而恰好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的一种发展方式.形而上学如同哈姆莱特的父王的幽灵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召唤一位历史性人物来“重整乾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后现代”思潮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冲动的彻底消失,假如“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灭使西方的逻各斯精神(包括逻辑精神)本身也遭到了彻底的覆灭,假如西方的努斯精神完全成了一种动物式的“怎么都行”的盲目冲撞,那将是人性的堕落和隳沉.我相信,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初衷决不会是这样,而是想要更大地发挥人的自发性的自由本性,摆脱现有一切规范性的束缚,把人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一些过激的提法,如对“人性”、“理性”等等基本规范的解构,只不过意味着他们对现有规范的不满和突破,而这种突破将不会是没有结果的,只是他们现在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果而已.
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所以,对于各个阶段上的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我们都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去研究他们、理解他们,为的是能真正超越他们.